人物艺术摄影:超越外貌,用影像挖掘人物的内在精神
我突然意识到,自己干了十年摄影,最珍贵的作品反而都诞生于这种“失控”时刻。就像三年前拍那个总把脸藏在刘海后的抑郁症女孩,她蜷缩在堆满药盒的出租屋窗边,阳光透过铁栏杆在她脸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伤痕。我本想用反光板补光,她却突然尖叫着打翻设备:“别用那东西照我!我就像只被扒了皮的虫子!”那天我们最终用了ISO1600的高噪点胶片,在完全自然光下拍了二十七卷——后来她盯着冲洗出的照片说:“原来我皱着的眉头里,藏着这么多没说出口的话。”

其实我刚入行时也迷信“完美脸庞”。二十二岁那年给某杂志拍封面,模特因为眼尾多了一颗痣要求重拍,我居然真的用遮瑕膏把它盖掉。结果成片出来,编辑指着照片骂:“这女的怎么像被抽走了魂?”那天我蹲在影棚后巷啃冷掉的煎饼果子,突然明白自己干了件多蠢的事——就像把一棵树的枝桠全砍掉,还怪它长得不够挺拔。后来我遇到那位总说“你拍出了我从未敢面对的自己”的中学老师,她指着照片里自己眼角的皱纹说:“这些沟壑里藏着三十年教书的疲惫,还有看见学生考上大学时的光。”
话说回来,真正让我从“拍美”转向“拍真”的,是2018年冬天那场设备故障。当时在废弃工厂拍一位独居老人,他正在给去世老伴的遗像擦灰,突然停电了。黑暗中我摸到相机包里的备用电池,却发现接口对不上型号。正慌神时,老人划亮火柴点蜡烛,跳动的火光在他脸上投下摇晃的阴影,那些皱纹像被风吹皱的湖水泛起涟漪。我顾不上对焦,直接按了快门——后来冲洗出的照片里,他浑浊的眼球里映着两簇火苗,嘴角还沾着没擦净的牙膏沫。这张“废片”反而成了那组作品里最戳人的,有位策展人看了说:“这哪是拍照?分明是往人心里扔石头。”
说到“废片”,我想起去年拍那位退休拳击手。他年轻时拿过全国冠军,现在经营着家小面馆,右手虎口还留着当年骨折的凸起。我本想拍他系围裙的“反差萌”,结果他非拽我去后厨,让我拍他揉面的动作。面粉扬起来时,我下意识调小光圈(就像让人摘下社交面具),他却突然停住:“等等!让我把手上的老茧拍清楚点。”那天我们拍了四百张,其中三百九十张都是虚的——他揉面的速度太快,相机根本抓不住。但有一张特别妙:他沾满面粉的手悬在半空,指节因常年握拳而变形,窗外救护车鸣笛声突然响起,他眼神闪了一下,那个瞬间被永远定格。后来他盯着这张照片说:“原来我放下拳套这么多年,骨子里还是那个要赢的混蛋。”
其实现在想想,技术这玩意儿就像做饭的调料——盐放多了齁得慌,放少了没味道。我见过太多摄影师扛着八万块的镜头,拍出来的照片却像超市促销传单。去年在摄影展遇到个同行,他指着我的作品说:“你这构图太随意了吧?”我指着他相机上贴的“大师滤镜参数表”笑:“您这参数调得比我家微波炉还精确,可照片里的人怎么像从流水线上下来的?”后来我们聊到凌晨三点,他突然说:“我拍了二十年人像,从没问过模特今天开不开心。”
说到共情力,我得讲讲那位总在凌晨三点给我发消息的姑娘。她是个酒吧驻唱,第一次来拍摄时穿着破洞牛仔裤,头发染成蓝绿色,脖子上挂着条银链子,上面挂着个迷你麦克风吊坠。我本想拍她弹吉他的侧脸,她却突然把吉他扔到一边:“别拍这个!拍我手上的茧,拍我膝盖上的淤青,拍我每次唱《后来》时喉咙里的血腥味。”那天我们拍了七个小时,最后她裹着我的外套蜷在沙发角落,眼睛红得像兔子。我注意到她手机屏保是张模糊的照片——应该是她前男友,但具体长相根本看不清。后来她成了我朋友圈的“深夜树洞”,直到某天突然消失,只留下条没发完的消息:“其实我最想让你拍...”
呃...这个支线好像跑偏了。反正那组照片里最戳我的,是张“失败”的作品:她唱到高音时突然破音,表情扭曲得像被踩了尾巴的猫,我手抖得连对焦环都拧不动,结果拍出来的照片里,她张大的嘴里能看见小舌在颤动,眼泪正从眼角滑落。这张虚焦的照片比任何“完美”的演唱照都真实——后来她在朋友圈说:“原来我狼狈的样子,也能被人当成宝贝。”
我相机包上贴着张泛黄的便签纸,上面写着“看见即慈悲”。这是五年前拍那位临终关怀护士时,她在我本子上写的。当时她刚送走一位癌症患者,坐在医院走廊里吃冷掉的包子,塑料袋上的油渍在灯光下泛着光。我本想拍她工作的样子,她却拉着我去病房,让我拍那位老人临终前攥着的女儿的手。“别拍脸,”她说,“拍手,手不会说谎。”那张照片里,老人枯枝般的手指深深掐进女儿掌心,女儿的指甲因为用力而发白,两人交握的手像两株在寒风中互相取暖的植物。后来护士告诉我,那位女儿后来成了志愿者,专门陪临终病人握手——“她说那双手的温度,能让她想起妈妈最后的爱。”
话说回来,我见过太多摄影师把“艺术”挂在嘴边,却连被摄者眼里的恐惧都看不见。去年拍那位单亲妈妈时,她五岁的儿子在旁边玩塑料恐龙,突然把玩具塞进她嘴里:“妈妈吃!”她笑着咬住恐龙尾巴,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疲惫的温柔。我正要按快门,她突然小声说:“能别拍我笑吗?我想让你拍我抱孩子时手在抖的样子。”那天我们用了最软的柔光(就像给伤口裹层纱布),她抱着儿子坐在地板上,阳光透过窗帘在她背上织出金色的网。我注意到她无名指上的戒痕还没完全消失,那是前夫留下的最后印记。后来她盯着照片说:“原来我假装坚强的样子,比哭还难看。”
其实现在想想,我花了五年才明白“真实比完美更重要”这个道理,可能有点笨但...反正我现在拍人,总先问三个问题:“你今天最想被记住的是什么?”“你最害怕别人看到什么?”“如果现在能撕掉一层皮,你想撕掉哪层?”有次拍那位总穿黑衣服的殡仪馆化妆师,她指着自己锁骨处的纹身说:“拍这个,这是我女儿的名字,她走的时候才七岁。”那天我们拍了很久,最后她突然说:“能给我拍张闭着眼睛的吗?我想让她看看,妈妈现在过得还好。”
我刚才说错了,不是光线问题,是氛围问题。就像那位总在菜市场卖花的阿姨,她每次摆摊都要把最蔫的花藏在最下面。有天我蹲在她摊位前拍她整理花束,她突然塞给我一枝快枯萎的玫瑰:“小兄弟,这朵送你了,它虽然不漂亮,但闻起来还有股甜味。”我举着那朵蔫头耷脑的花,突然明白摄影的真谛不是捕捉光鲜,而是记录那些即将消逝却依然努力绽放的瞬间。后来我把这张照片洗出来送给她,她贴在摊位上,旁边写着:“烂玫瑰也是玫瑰。”
最后想说说“技术至上论”。有位非著名摄影师说过:“好的照片不是拍出来的,是长出来的。”就像种庄稼,你得先松土、浇水、施肥,然后等着它自己发芽。我见过太多人举着顶级相机,却拍不出一张有温度的照片——因为他们忘了,镜头后面那双眼睛,才是最重要的“设备”。就像我那位总说“你拍出了我从未敢面对的自己”的中学老师,她后来在信里写:“以前我觉得皱纹是敌人,现在才明白,它们是我活过的证据。”
现在我的相机包里永远装着三样东西:备用电池、纸巾(总有人拍着拍着就哭了),还有本破旧的笔记本,上面记着被摄者们说过的话。有句话我特别喜欢,是那位退休拳击手在照片背面写的:“拳头会软,但心里的火不能灭。”呃...怎么说呢,摄影这事儿,说简单也简单,说难也难——简单到只需按下快门,难到要花一辈子去学会“看见”。就像我相机包上那句“看见即慈悲”,有时候你不需要多高的技术,只需要多一点的耐心,和一颗愿意蹲下来听故事的心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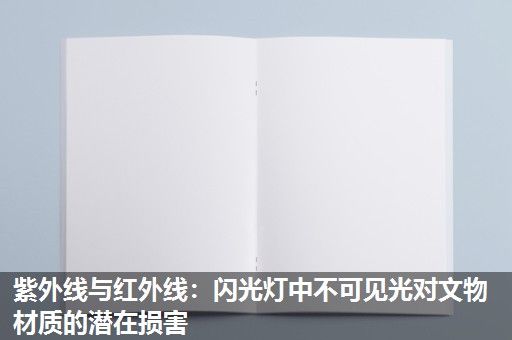



0 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