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苏SWC测评经典中画幅旁轴相机收藏、拍摄价值分析
“1962年的A型,”老板说,“刚收的,品相不错。”我伸手去摸,指尖刚碰到机身,心里“咯噔”一下——这手感,绝了!金属的凉意混着皮革的温润,从指尖窜到后颈,像摸到了一块老玉。取景器凑近眼睛的瞬间,我愣住了:眼前突然亮得像开了扇窗,连对面墙上剥落的墙皮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老板在旁边笑:“旁轴取景,所见即所得,哈苏把这玩意儿玩到顶了。”

那天我没带够钱,站在柜台前磨了半小时,最后把刚买的数码单反退了,揣着SWC出了门。路上抱着它,像抱着个刚捡到的宝贝,生怕磕着碰着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台A型是SWC的初代改进版,产量不过几千台,而我,成了它新的主人。
拍摄:镜头里的魔法
真正带它出门拍,才发现这镜头有多毒。那支Biogon 38mm f/4.5,从中心到边缘的分辨率,哪怕放在今天的中画幅数码后背上,也毫不逊色。我试过用它拍敦煌的星空——凌晨三点,戈壁滩上冷得直哆嗦,我支起三脚架,把SWC架好,取景器里,银河像条银色的河,从地平线一直淌到头顶。对焦环拧到无限远时,能听见镜头里“咔”一声轻响,像锁住了整个宇宙。按下快门的瞬间,快门声轻得像猫走路,连风声都没盖住。
后来冲出来,底片上的星星颗颗分明,连银河的暗带都清晰可见。数码相机再好,也拍不出这种“呼吸感”——胶片的颗粒在暗部微微发亮,像撒了把细盐,而SWC的镜头,把这层质感保留得恰到好处。有次在婺源拍清晨的雾气,阳光刚透进来,雾里泛着淡紫色,SWC的色彩还原绝了——不是数码那种直白的鲜艳,而是像被水洇过的水彩,柔和里带着层次。后来我拿数码相机拍同场景,怎么调参数都调不出那种味道,最后只能认输:“这镜头,毒!太毒了!”
不过话说回来,SWC的取景器在暗光下确实有点局限。有次在胡同里拍夜景,天全黑了,取景器里黑得像口井,只能凭感觉构图。结果冲出来,发现屋檐的飞角只拍进去一半,气得我直拍大腿。但这也是旁轴的通病——没有五棱镜的加持,暗光下确实吃力。不过换个角度想,这种“不完美”反而成了它的特点——就像老电影里的胶片划痕,成了时光的印记。
机身设计也有意思。SWC的机身特别薄,比大多数中画幅都轻,背在包里像揣了本硬皮书。但操作起来又特别“硬核”——没有自动对焦,没有曝光补偿,连测光都得靠外接。有次在黄山拍云海,我忘了带测光表,只能凭经验估光,结果冲出来全欠曝了。后来我学乖了,每次出门都揣着本测光手册,像揣着本武功秘籍。
但这种“麻烦”反而让我更爱它——拍摄变成了种仪式感。每次按快门前,都得先调光圈、对焦、构图,再确认测光,最后才轻轻按下快门。整个过程像在跟相机对话,而不是单纯地“记录”。数码相机按快门太容易了,容易让人忘了拍摄的本质——而SWC,逼着你慢下来,去感受每一束光,每一片影。
收藏:时间给的礼物
后来我收了三台SWC,每台都有故事。第一台是那台1962年的A型,机身编号#2347,取景器里有点划痕,老板说这是“使用痕迹”,我反而觉得这划痕像道年轮,记录着它走过的路。第二台是1978年的C型,限量版,机身是黑色的,比普通版更稀少。我收它的时候,卖家是个老摄影师,临走前说了句:“这相机跟了我二十年,拍过婚礼,拍过战争,现在老了,拍不动了,你替我接着拍吧。”我抱着那台C型,突然觉得手里的不是相机,是个传家宝。
第三台是1989年的M型,最后一批SWC,也是最完善的一代。我收它的时候闹了个笑话——在拍卖会上,我跟另一个藏家杠上了,他出到两万八,我咬咬牙喊了三万。结果拍下来才发现,这台的快门帘有点老化,得送去修。朋友笑我“冲动”,我挠挠头说:“没办法,看到那支Biogon镜头,就走不动道了。”
收藏SWC,最头疼的是辨别翻新机。有次我在网上看到一台“全新SWC”,价格低得离谱,卖家说是“库存机”。我让他拍机身编号,结果编号是刻上去的,不是原厂的压印——哈苏的编号都是用模具压的,边缘有自然的毛刺,翻新的刻得太规整,一看就是假的。还有次,我收到一台“品相完美”的SWC,取景器亮得像新的一样,结果冲出来底片边缘有暗角——后来才知道,这台的镜头镀膜被换过,原厂的镀膜在逆光下会有种独特的反光,像层薄雾,翻新的则亮得刺眼。
不过话说回来,收藏SWC的乐趣,也在于这种“淘宝”的过程。每次收到一台新机,都得像侦探一样,从机身编号到镜头镀膜,从快门声音到取景器亮度,一点点验证它的“身份”。有时候找到一台真品,比拍到一张好照片还让人兴奋——毕竟,这不仅是台相机,更是段历史。
那些年,SWC陪我的瞬间
有张照片我特别喜欢,是2018年在婺源拍的。那天清晨下过雨,雾气还没散,我背着SWC钻进一条老胡同。阳光从屋檐缝里漏下来,照在青石板上,雾气泛着淡紫色,像层薄纱。我支起三脚架,把SWC架好,取景器里,雾气里的老屋像幅水墨画,连屋檐滴下的水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按下快门的瞬间,快门帘“唰”地打开,又“唰”地合上,像一声轻叹。
后来冲出来,底片上的雾气像活了过来,轻轻飘着,连水珠的轨迹都清晰可见。我把这张照片洗成16寸,挂在书房里,每次看到它,都像回到那个清晨——背着SWC,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,听着雾气里的鸟鸣,感觉自己像个时间的旅人。
还有张是在敦煌拍的星空。那天晚上,我裹着睡袋躺在戈壁滩上,SWC架在三脚架上,镜头对着银河。取景器里,星星像撒了把碎钻,亮得晃眼。我调好光圈,对焦到无限远,轻轻按下快门。快门声轻得像片落叶,却在我心里砸出了个坑——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爱这台相机。
它不是最快的,不是最轻的,甚至不是最方便的,但它让我重新爱上了拍摄——不是为了“记录”,而是为了“感受”。每次摸到它,都像回到二十岁那年,背着相机满世界跑的日子——那时候,拍摄是件纯粹的事,没有参数,没有算法,只有光,和一颗愿意等待的心。
尾声:一台相机的重量
现在,我的书架上摆着三台SWC,A型、C型、M型,像三个老朋友,静静地看着我。有时候我会把它们拿出来,擦一擦镜头,转一转对焦环,听听快门帘“唰唰”的声音——这声音,像首老歌,唱了六十年,还没唱完。
朋友问我:“都数码时代了,还玩胶片,不累吗?”我笑笑,没说话。其实我也说不清为什么爱它,可能就是…缘分吧。有些相机,不只是工具,更是伙伴——它陪你看过日出,拍过星空,记录过时光的痕迹,也见证过你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。
这张《胡同晨雾》,就是SWC留给我的时间胶囊。每次看到它,我都想起那个清晨,想起雾气里的老屋,想起取景器里的那片星空,想起自己背着相机,走在路上的样子——那时候,我以为自己在拍世界,后来才发现,世界也在拍我。
而SWC,就是那台最懂我的相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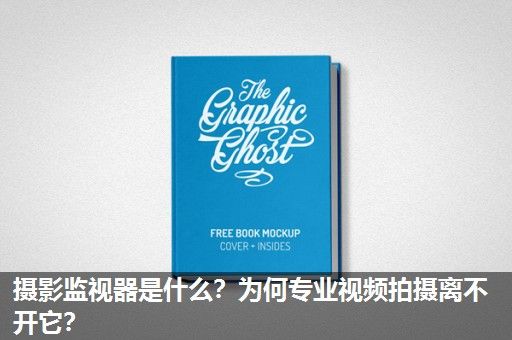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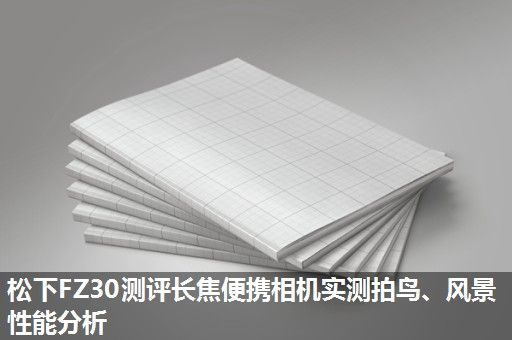

0 留言